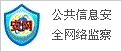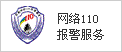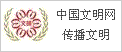人民交通讯(韩杨)货币的本质是什么?这一问题贯穿了经济学史的始终。传统经济学将货币定义为“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”,现代主流观点则聚焦其“交易媒介、价值储藏、记账单位”的职能集合,而余求宝教授提出的“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可编程承诺”,为数字时代的货币定义提供了新范式。这一定义是否科学?其与不同时代的货币认知有何关联?我们需要从货币的本质属性、历史演进与数字特性中寻找答案。
一、“可编程承诺”的科学性:抓住货币的信用本质与技术内核
判断一个定义的科学性,关键在于其是否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,并对其历史形态与未来演进具有解释力。余求宝教授的定义包含三个核心维度:跨时空性(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价值转移)、价值交换(货币的核心功能)、可编程性(规则化、可执行的承诺载体)。这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了货币的本质——信用的具象化。
从历史维度看,货币的演进始终是信用形态的升级:实物货币(如贝壳、金属)的信用基于其物理属性的稀缺性;信用货币(如纸币)的信用基于国家主权背书;数字货币(如CBDC、稳定币)的信用则基于技术规则(如区块链共识、智能合约)。无论形态如何变化,货币的核心功能都是“记录并执行跨时空的价值承诺”:农民用粮食换货币,本质是“用现在的劳动换取未来购买工具的承诺”;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,本质是“用本国商品换取跨越国界的价值认可承诺”。
而“可编程性”恰恰揭示了数字时代信用的新形态。传统货币的“承诺规则”(如支付限额、兑换比例)依赖人工执行,而数字货币的规则可以通过代码固化(如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支付条件)。这种“可编程性”不是对货币本质的偏离,而是信用载体从“物理媒介”向“数字规则”进化的必然结果。因此,“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可编程承诺”既抓住了货币“信用本质”的共性,又体现了数字时代“技术载体”的特性,具备科学性。
二、与传统定义的异同:从“等价物”到“承诺”的认知深化
传统经济学对货币的经典定义是“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”(马克思),其核心是将货币视为“商品交换的媒介”,强调其“等价性”(即货币本身具有价值,如金银)。这一定义与“可编程承诺”的差异,本质是对货币本质认知的“从物到信”的升级。
——相同点:
二者都承认货币是价值交换的载体,都服务于跨时空的经济活动(如金属货币通过窖藏实现价值跨时间转移,通过贸易实现跨空间转移)。
——差异点:
- 本质认知不同:传统定义将货币视为“有价值的商品”,其信用基于自身的物理价值;而“可编程承诺”将货币视为“信用符号”,其价值不依赖自身属性,而依赖承诺的可信度(如纸币本身无价值,但国家信用使其成为有效承诺)。
- 适用范围不同:传统定义仅能解释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,无法解释信用货币(纸币本身不是商品)与数字货币(纯数字符号,无物理价值);而“可编程承诺”可覆盖所有货币形态——金属货币的“承诺”基于其稀缺性规则,纸币的“承诺”基于法律规则,数字货币的“承诺”基于代码规则。
- 时代局限性:传统定义诞生于商品经济主导的时代,强调“等价交换”的物质基础;而“可编程承诺”更适应信用经济与数字经济,突出货币作为“社会共识”的非物质属性。
三、与现代主流观点的分野:从“职能集合”到“本质抽象”
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从“职能”定义货币,即“同时具备交易媒介、价值储藏、记账单位职能的物品”(弗里德曼等)。这种定义跳出了“商品属性”的局限,更注重货币的功能表现,但仍未触及本质。
——相同点:
二者都认可货币的跨时空功能(价值储藏对应跨时间,交易媒介对应跨空间),都承认货币是经济活动的“润滑剂”。
——差异点:
- 认知层次不同:现代主流观点是“功能描述”,而“可编程承诺”是“本质抽象”。职能是本质的外在表现(如“交易媒介”是“跨时空承诺”的即时执行形态,“价值储藏”是“跨时空承诺”的延时执行形态),本质比职能更具解释力。
- 技术敏感度不同:现代主流观点形成于电子货币时代,未充分考虑数字货币的“可编程性”。例如,传统职能定义难以解释比特币的“智能合约支付”(需满足代码条件才能执行),而“可编程承诺”直接点出其规则化执行的核心。
- 优劣对比:职能定义直观易懂,便于分析货币的经济影响;但“可编程承诺”更能预判货币形态的演进——当“承诺”可以通过代码自动执行时,货币的职能(如支付、借贷)将被重构(如DeFi中的自动借贷)。
四、与数字货币的契合:定义对数字时代的前瞻解释力
数字货币(包括加密货币、CBDC、稳定币)的崛起,是检验货币定义科学性的“试金石”。“可编程承诺”与数字货币的特性高度契合,而传统定义与现代主流观点则显露出解释力不足。
——相同点:无论数字货币还是传统货币,核心功能都是价值交换,都依赖社会共识(信用)。
——差异点:
- 跨时空性的突破:传统货币的跨时空交换依赖物理运输(如金银)或中心化机构(如银行转账),效率低且成本高;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等技术,可实现全球实时清算(如比特币10分钟确认跨国界交易,稳定币在跨境电商、即时支付等方面优势明显),其“跨时空性”是技术原生的,而非依赖外部体系。
- 可编程性的深度融合:数字货币的“智能合约”特性使其成为天然的“可编程承诺”——例如,央行数字货币(CBDC)可嵌入“定向支付”代码(如仅能用于教育支出),稳定币可通过代码自动锚定法币汇率。这种“承诺”的执行不依赖人工,而是由技术规则保证,这正是“可编程”的核心体现。
- 信用载体的变化:传统货币的信用载体是“国家”或“机构”,数字货币的信用载体则是“技术规则+社会共识”(如比特币的信用基于区块链不可篡改规则与全球矿工共识)。“可编程承诺”直接揭示了这种信用载体的转型。
相比之下,传统定义无法解释“无实物价值的数字货币为何能流通”,现代职能定义难以说明“智能合约如何重构货币职能”,而“可编程承诺”则完美覆盖了数字货币的技术特性与本质属性。
五、结论:定义的演进是货币形态进化的镜像
从“一般等价物”到“职能集合”,再到“可编程承诺”,货币定义的变迁本质是货币形态从“物质载体”向“数字规则”进化的镜像。余求宝教授的定义之所以科学,在于其既保留了货币“跨时空价值交换”的核心功能,又以“可编程承诺”捕捉了数字时代信用载体的技术特性——它不是对传统定义的否定,而是在信用经济与数字技术融合背景下的认知升级。
当然,任何定义都有其语境限制:“可编程”在实物货币时代更多体现为“约定俗成的规则”(如金属货币的成色标准),在数字时代则体现为“代码化的自动执行”,这种广义理解使其具备普遍性。未来,随着货币形态进一步进化(如央行数字货币与物联网的融合),“可编程承诺”的内涵还将继续丰富,但这恰恰证明了其抓住本质的科学性——定义的生命力,正在于对变化的解释力。
(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、世界预经济科学研究院数字货币与新型金融研究课题组)
(编辑:韩杨)
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30064号 京ICP备18014261号-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:(京)字第16597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602130064号 京ICP备18014261号-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:(京)字第16597号